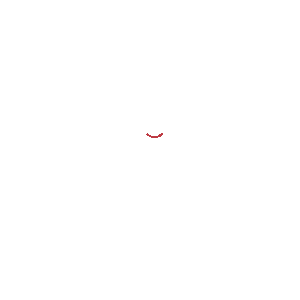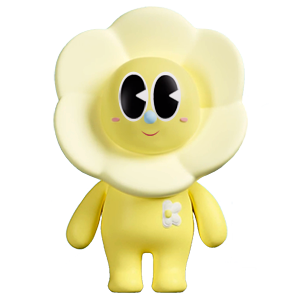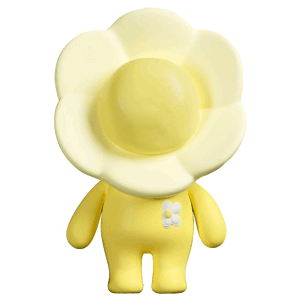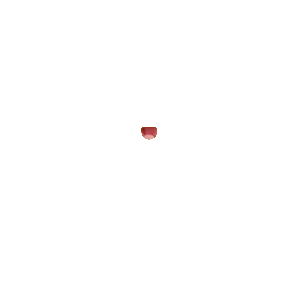每年的农历冬月十八是母亲的祭日,母亲离开我已经整整18年了。好多日子过去了我对母亲的思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淡化,我一次次回忆往事,在她逝去的日子里,每每想起都让我两眼湿润,不禁落泪。
从记事起,我就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我排行老四,也是独子,家里的状况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听母亲给我讲,解放初她在界岭道班女子民兵连修路,父亲当时在街政府工作,和父亲结婚后几年没有生育,在56年大女儿出生,一年后母亲又生了一个女儿,由于要工作,大女儿就交给奶奶照管,二女儿带到界岭,在二女儿不满两岁时不幸落水夭折。奶奶重男轻女,嫌弃母亲没有生男孩,百般折磨大女儿,不给她饭吃,让她流落街头检食。有好心的街坊实在看不下去就给母亲捎信说,要是母亲再不回去恐怕大女也要被饿死。母亲不得不放下工作回家照护,从此再也没有了正式工作。
60年代初,我们就从大家庭分家租住在清风沟高家屋内一间不足8平米的房子,进门就是床,做饭在后阴沟房檐下,只有一个缸缸灶,雨天母亲就戴草帽做饭。分家时奶奶只给了母亲娘家陪嫁的一张小桌和一个抽屉桌,床是两个长条板凳支的,床板是母亲自己用小竹条编制的竹笆,一家几口都挤在一张床上,当晚床就睡垮了。母亲娘家原来在上河开银铺,解放初被逼下放农村,房产全部没收,不久回城后,没有住处,政府发的粮本又不幸遗失,由于成分不好,政府不给补发,外公外婆相继饮恨怄气而死。奶奶嫌母亲的娘家穷又是下放户不愿周济,几个兄弟也在59年和60年间全国饿饭时期饿死,只剩下一个兄弟在街头乞讨和给人家挑水为生,晚上就到破旧的魁星楼露宿。1965年西安红旗电机厂在白河招工,街政府的领导可怜我这唯一的舅舅,就把他送走,母亲也就不再为此操心。
我的出世给母亲带来了莫大欣慰,改写了只会生女娃的历史。我是在66年出生的,正逢全国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父亲就给我起名红,母亲没有文化,只是在婚后上过几天自习班,我们姊妹几个的名字都是父亲起的。听他讲这个红一是想掩盖当时家庭成分高,二是表示要又红又专,积极响应”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号召。其实在我上学的时候,同学们都讥笑我是女娃子的名字,笑我们家女娃多男娃少,但我一直把这个没有给我带来好运的名字用到了现在都没有更改。
60年代末,铁道兵在清风沟一沟两面坡驻扎,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就在一号隧道推矿车倒矿渣,父亲已经在县物资局工作。直到有一天,母亲被工友送回家,后来听大人们说是风湿,是由于在阴暗潮湿的隧道里时间长了致下的,从此母亲再也干不了活,为了生计,减轻父亲的压力,大姐辍学到处打零工挣钱供弟妹读书和帮补家用。
虽说母亲身体不好在家休养,却一点也没有增添家庭负担,她除了支撑着料理全家的一切家务,还带着我检石头砸石子卖,平时一家老小吃的、穿的都是母亲一人经管,母亲很聪明能干,家里的生活用品基本上都是母亲的手工制作,这样也节省了很大的开支,父亲的一点微薄工资让她计算的有条有理,没有让一个子女饿着、冻着。
母亲身体不好,却嗜好烟、茶。我记事起她就抽烟,而且烟瘾很大。听母亲自己说是在界岭道班学会的,后来就上瘾了。由于条件不允许,母亲只能抽当时最低廉的“万山”或“羊群”牌的,只有在家中来贵客时才偶尔买一包“丹江”、“鸿雁”。为了节省开支,我就沿街给母亲检烟头回去,母亲把我捡回的烟头经过整理后搭着抽。对门住的巴运旺叔叔非常喜欢我,他的工作是在电影院门口守门收票,每天晚上他上班时都叫我跟他一起去看电影,那时放的都是些革命样板戏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不是《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就是《勇敢的人们》、《伏击战》等,而且是长年不变,所以我去电影院根本就不想看电影,主要目的是在观众陆续进场正片开始前放《新闻简报》时,好在长木椅下搜寻烟头,每天捡的烟头要分成两份,一份先给爷爷送去,一份回去交给母亲。
母亲抽烟的习惯,奶奶和叔叔、姑姑们都很反感。小时候我喜欢到奶奶那去玩,他们都当着我的面骂母亲是“女特务”,每当这时我都不舒服,只有默默不语,虽说我还不很董事,可我一直对母亲抽烟没有反对过,而且我知道母亲内心很苦而且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所以对别人说她什么我都不屑一顾。
由于贫穷,母亲的心里压力很大,脾气很坏,对除了会上班工作外几乎什么家务都不会做的父亲吵起来经常是没完没了,父亲知道母亲的苦处,身体又不好,只好默默的忍受。但母亲对子女,却从不发脾气,也没有任何偏袒,都一样心疼。
1973年夏,随着铁路的通车,铁道兵渐渐撤走,在父亲的要求下,县上给我们分了一间铁道兵留下的居民点的土房屋,三家共用一个小天井院做厨房,从此我们的住房条件有了很大改善。由于正房只有一间土房,几个姐姐都大了,母亲就用竹笆把它隔成三间,还自己挖了一个地炉取暖,这种地炉在附近居民家庭很快就推广使用,这是母亲的一个小小发明。每逢过年母亲就忙着用报纸糊墙,就这样糊了一层又一层,在这里一住就是13年。
在居民点住的时候我和两个姐姐都上学了,我已经上小学二年级,妹妹上幼儿园,家里的经济更加困难。学校都是半日制,当时城关的小学和中学都在建设之中,我和两个姐姐除了参加学校的义务劳动之外,利用所有的课余时间下河挑砂、砸石子卖、在码头上挑砖、一起到小河口食堂的垃圾堆和下卡子石灰窑捡烧剩的煤煳。由于贫困,父亲在每学期给我们报名前都给我们在居委会老奶奶那开好免学费的证明,这样我们上小学就只需要书本钱了。
搬到居民点后不久爷爷就因病去世了,当时文革还在轰轰烈烈的进行。由于贫穷,父亲是个胆小怕事的人,所以一切都从简,既不戴孝,也不敢放鞭炮,安葬的坟地也是公路村无偿给安排的,在爷爷去世的第二天就草草的安葬了。
1978年下半年,我的大姐病倒了,由于太穷,没有钱去医院医治,为了省钱,母亲四处找草药医生到家里给大姐看病。当时传说蜀河有“红军老总”显灵,就让大姐带上香表徒步去蜀河祭奠许愿治病,带回些灵药服用,那次回来大姐的腿脚都肿了,母亲心疼的不住流泪。1979年4月,大姐的病情恶化,不得不到十堰张湾医院医治,医生检查后得知,大姐患的是肺结核肿瘤,必须尽快做手术。父亲就到大姐所在的平顶山林场借钱,又放下工作请假到十堰张湾医院陪护,这样一住就是半年。父亲因此由于请假时间超过三个月、向单位借钱多的缘故,在以后的几次调资中都被取消了资格,本来就很贫困的家里生活更加困难了。
在大姐住院期间,隔壁邻居周帮维出差回来告诉母亲说大姐的第一次手术由于天气炎热感染不能愈合,还要进行二次手术。母亲听后面无血色,几乎晕倒在地。当时交通不便,又没有通讯条件,母亲无法了解大姐的病情。母亲毅然决定要亲自去医院看看,我正好放暑假,就带上我乘火车去十堰。母亲没有出过门,也没有坐过火车,也不知道十堰在哪里,更不知道在哪里下车,我和母亲一样是四门天黑,就跟着母亲离十堰还有很远就下了车,下车一问才知还没有到十堰,这时火车已走远,我和母亲只好焦急的在公路上急步向十堰方向行走。记得那天烈日炎炎,那时虽说我只有13岁,我已经很懂事,很能理解母亲是由于着急才神智恍惚的,我跟着母亲默默的走,在母亲面前没有表现一点怨言。就这样在烈日下我们母子一起走了近20里地时候,突然在我们身后传来汽车的马达声,母亲就像发现了一根救命稻草,拼命的拦在路中央,汽车不得不停下来,母亲告诉司机师傅说我们下错了车,要到十堰去,司机师傅可怜我们就让我们上车,把我们带到了十堰。到十堰找到了大姐住的病房,正好看到医生在给大姐清理感染的伤口,伤口很长很深,就像一张大嘴张开着,母亲流着眼泪让我不要看。为了省钱,我和母亲借住在一个攀上的白河老乡家里,房屋相当破旧,强免可以栖身,那次在十堰一住就是四天。
1983年7月31日,我参加完高考后不久,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席卷县城河街,老家的两间房子被水打的片瓦不留。洪水过后,奶奶接到我们家有母亲照管,母亲组织家人清理地基上堆积的淤泥,十几人的吃喝由母亲一人经管。当时母亲想在原址上兴建房屋做点小生意,谁知两个叔父怕母亲要分房产,在清理完屋基后迅速将屋基悄悄的溅卖了。母亲得知后非常生气,和奶奶、叔父据理力争,但由于父亲是个孝子,在父亲的再三劝说下,才分给我们家200块钱卖屋基款了结了此事,奶奶在我们家住了半年后就移居到二叔家。
1983年秋季开学后,高考通知终于来了,我被陕西省商业学校录取。母亲看到学校的通知后比我还高兴,就赶紧上街给我买这买那的准备,几乎把我要用的东西都买齐了。由于商校开学晚,该走的都已经走了,我没有出过门母亲放心不下,就到处打听给我找熟人带我一起走。那时交通不便,到火车站只能坐船,母亲就一直把我送到红星桥下汉江码头,才含着眼泪望着我乘船离开。在我每学期放假回家,母亲总是在我们居住的居民点前排的石坎上张望。记得是我第一个寒假回家,母亲拉着我一路走一路问在学校的情况,走进家门,母亲急忙在大皮箱里翻,很久才操出个用报纸包着的园东西来,笑着递给我说,你的几个姐姐和妹妹我都没有舍得给他们吃,专门留给你吃。我接过手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个烂得无法再吃的苹果,我愣了半天,欲哭不能,只好忍着眼泪,怪母亲怎么舍不得吃,非要放坏了才甘心!
1985年7月我毕业前夕,得知我被分配在原安康地区外贸公司,我就写信给家里,父亲给我回信说,母亲死活不允许在外面工作,必须回到她身边。无奈我只好请学校把我派遣回到县上工作了。
1988年9月14日,我的三姐突然意外离世,给母亲的打击很大,使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整天以泪洗面。亲戚朋友都上门和母亲聊天解劝,并提出要想让母亲早点从失去女儿的阴影中走出来,就尽快给我找个媳妇,以此来安慰母亲的殇女之痛。
在两个姐姐的张罗下,在1989年4月初,经人介绍我和她相识了,并很快在1990年结婚。作为母亲唯一的儿子结婚成家,着实对母亲是一个最大的安慰,从此,母亲总是微笑着看着我们小两口,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似乎忘记了殇女之痛,整天拖着瘦弱的身体忙着照护我们,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农历1991年冬月18日临晨5时,那天,我守在母亲的床边,母亲走的那么安详,那么平静。这是一个对我非常残酷的日子。我痛恨癌症,它居然这么残酷地夺去了母亲的生命。她才60岁啊,就这样飘然而去,她还远远还没有活够、还没有等到看一眼她的孙子啊!
岁月无痕,母爱无声。因为能承受的,母亲都承受了,该付出的,母亲都付出了。
在我人生的历程中,有过磨难和失意,但有我永远爱着、想着我的母亲,让我感到无比的坚强和自豪。我爱我的母亲、我的老母亲,在我眼里母爱是一种永远值得洒泪的感怀,是一篇总也读不完的美好故事。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
点击我为您语音播报